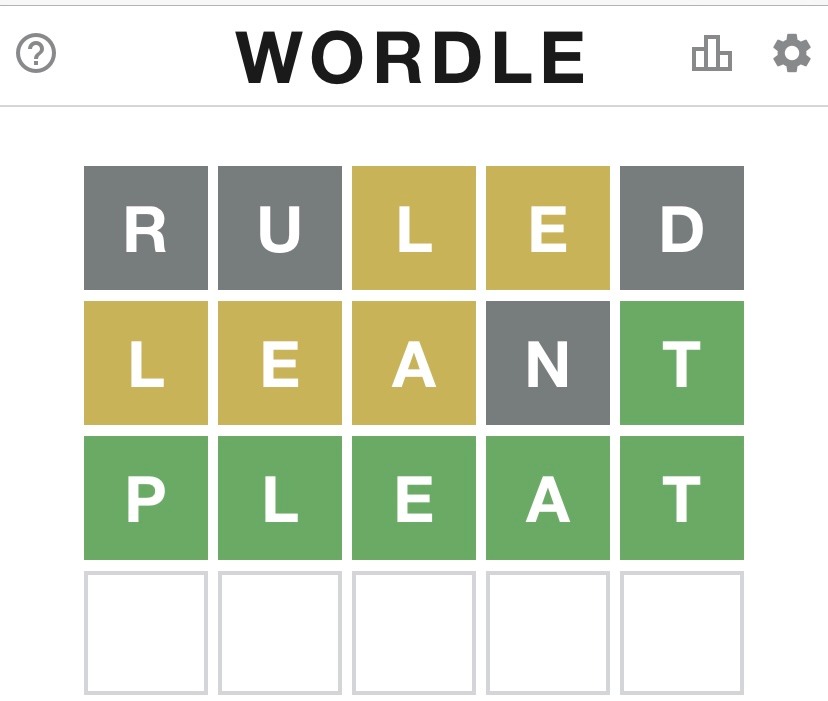Photo Credit: Christophe TONG Yui
(薪傳文社社員。曾獲大學文學獎詩、小說獎及青年文學獎散文、兒童文學等獎項。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學士 (主修美術) 巴黎第三大學──新索邦大學法國文學學士、比較文學碩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小說《Footnotes》曾獲「年輕作家創作獎」,及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現為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另譯有《行腳商》(散文)一書。)
課堂結束後,W 興高采烈地來到講壇前面。
我在課上所提及的動漫,對於學生一代來說,可能已經有點舊,但 W 對部分作品的內容,竟然知之甚詳,這不禁讓我有點意外。
「是的,我師父也曾向我推介過這些作品。」
原來W 在校外,也通過各種渠道,學習寫作和攝影。
文圈有不少認識的文友,都在教寫作,於是我想,W 的師父,會不會恰巧是哪位認識的朋友。
「你恐怕不認識他,嚴格來說,他並非文圈中人。」
但我還是禁不住好奇,繼續追問,於是 W 說出了一個名字。
那確實並非文圈裡的朋友,卻是我知道的名字。
我立即問 W ,他怎麼會認識這位師父。這倒輪到 W 好奇我怎麼會聽過他師父的名字。
「他是我中學的師兄。」我說。
「噢,你原來也在那裡畢業。」W 說。
事情愈來愈玄……
我們的中學,並非那種一提名字,就會讓人發出「噢,原來是那間」的名校,但聽 W 的語氣,他彷彿對我的中學非常熟悉。
「那當然,我在那裡長大。」
母校是一所教會學校,經 W 這麼一說,我開始思疑,他和家人,會否恰巧就是母校教會的教友。如果屬實,那真是太巧了,因為據我所知,母校教會的教友為數並不算非常之多,能夠湊巧讓我在課上遇上的機率,可說是非常之低。
然而,現實竟比我想像的更離奇。
「我爸爸是那裡的老師。」被問及跟我母校的關係時,W 理直氣壯地這麼說。
竟有這麼巧恰的事?我順理成章向 W 打聽他父親的名字。
那真是個久違的名字……
W 的父親並沒有任教過我,而且就在我入學的翌年左右,他就轉職到其他中學,然而這位老師的名字,卻因為一些事情,鮮明地保存在我的意識之中。
現在的中學如何,已經不太清楚,但那時中學的操場早會,是會有突擊檢查儀容和書包的環節。香菸、色情書刊或者其他違法物品,當然是絕對不行。然而,在那物質遠沒有今天豐富,娛樂生活仍然非常仰賴實物交流的年代,同學之間,有時為了交流興趣——特別是流行或次文化方面的興趣,卻會冒著被記過和沒收的風險,偷偷帶上一大堆今天回想起來,可能均屬無傷大雅的「違禁品」回校。這些東西包括Walkman 或者Discman,錄音帶和CD;潮流雜誌或者唱片;明星海報和照片;遊戲機、遊戲匣帶,電玩周邊產物,乃至曾經風靡一代人的——「他媽哥池」養雞機;此外更為大宗的,相信就是從動漫屋租借或者買入的漫畫和錄影帶,還有海報、閃卡或者首辦模型等數不盡的延伸物品。
對於剛入學的中一生而言,總難免會遇上這樣的倒霉日子。
當你跟幾位剛開始熟稔的同學,三三兩兩,男男女女,捧著排球,興高采烈,準備在放學後的操場聯誼一番之時,竟發現無論是有蓋或沒蓋的操場,均已被校隊佔用,而狹仄校舍的邊緣地帶——操場邊的走道或者後閘旁邊的廢棄物料場,也早塞滿比你們高一到六年的前輩時,你們實在不得不冒著被屋邨童黨騷擾的風險,到學校附近破敗的球場,一圓那卑微的願望。
排球懸起在半空時,你忽然想起,《龍珠》裡的孫悟空,已搖身一變,成為傳說中的超級撒亞人好一段日子,於是你就到邨裡的書報攤,將那搖搖欲墜的娜美星,搬到球埸一角搖搖欲墜的長椅上仔細端詳。奸角菲利被自己的傲氣一刀兩斷的瞬間,你瞥見一張似曾相識的身影步進球場。菲利的太空船,原來已破損得無法啟動,悟空哀傷地對你說,要爆炸了,眼下是逃不掉了。結果,你只好乖乖讓巡邨的訓導老師扣押你的漫畫,並答應在翌日的小息主動到教員室投案。
你其實曾經暗自盤算,要不要悄悄逃掉。因為,對於從未任教過你的老師,即使在校內再次碰見,他恐怕也無法將你一眼認出。只是,考慮到罪加一等的可能,你最後還是老實帶著手冊,踟躕地踱到教員室,等候發落。
「我翻了一下書的內容,裡面並沒有甚麼不良意識。」
你頓時鬆了一口氣,準備把一早翻開的手冊闔上。
「不過你穿著校服在邨裡無所事事地留連,多少還是會損害學校的形象……」
好吧,剛才手冊翻開的那頁是……。
「這次我沒打算寫你的手冊,但在交還漫畫給你之前,我想你先給我寫一篇作文,談談看漫畫的好處與壞處。」
那篇有關漫畫的作文,到底寫了甚麼,已經亳無印象。翌日取回漫畫的時候,我只記得,這位從未任教過我的老師,跟我上了饒富意義的一課。
相對於恫嚇,教育的意義,其實更在於幫學生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離開教員室之後,我一路翻著我的漫畫,然後將它帶到了我的寫作教室,並且胡里胡塗地,遞了給老師的孩子。
W 翌日跟我說︰「我爸竟說他已毫無印象。」
這是在所難免的。
那篇有關漫畫的作文,少說已經丟失了二十多年,文中到底寫了些甚麼,我們肯定都已毫無印象。幸好漫畫的其中一項優點是,它會不住地為我們講述故事,在文本之內,還有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