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圍的景色已到十分模糊,發生過甚麼事了?我已經不太記得了。仍在腦海中浮浮沉沉的是一位少年目無表情,冷冰冰的臉龐。他的四肢無力,看起來疲憊不堪。有點黝黑的雙臂彷彿被地下拉著,手掌向上的,靜靜地垂到地上;他的背彎彎的,頸子微微向前傾;他像被石化了般,一動不動的維持著跪在地上的姿勢,只用瘦弱的大腿支撐起整個人,就像曾嘗試站起身子,卻又被重力狠狠的拉住,束縛住。那時的我好像能理解發生甚麼事,就像能在沒有溫度的石頭中感受到如地獄般的痛苦般,我用手向地下奮力一推,柔弱的身子隨之而動了起來,背脊像被大力推了一把,雙腳踏著瞬速又沉動的步伐。我如離弦之箭般衝到少年的面前,然後毫不猶豫的把少年抱入懷中。從他柔軟的黑髮中,傳來了一點點溫度。「沒事了,已經沒事了。」我把頭輕輕靠在了少年的頭頂,雙手放在了他的後頸,我似乎深陷在他逐漸恢復的體溫中。以他駝背跪在地上的高度,似乎能聽到我的心跳。「呯,呯,呯⋯⋯」。我似乎也能聽到。「已經沒事了,我來了。」。我緊緊地擁抱著他,緩緩地閉上了雙眼。
隨後,我在一片黑暗中聽到刺耳的鈴聲,當我再次睜眼時,映入眼簾的是被撒上過份耀眼的陽光的,我寢室那雪白的天花板。這一刻,我的思考能力似乎仍未醒來,沒有阻止我再次合上眼睛,就像我必定能回到那少年身邊一樣,但我已經睡不著了。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撐起了我的身子,手中似乎仍殘留著少年那微暖的體溫。我沒有下床,只盤著腿靜靜地坐在被烈日佔據的單人床上。這時我輕輕伸出了雙手,把手臂往上提,用手把身前的空氣圍了起來,又轉了轉頸子,面向一旁,把頭朝手掌所在的方向傾了傾,但又在中途停了下來,彷彿在擁抱著甚麼。「很溫暖。」明明只是剛剛睡醒還沒開聲,我卻忍不住如此說道。
這位少年在現實中向我表白了,我猶豫了很久,更向友人求助,我本想答應他,但一鼓不知名的感覺,在我耳邊輕聲勸我拒絕。這種感覺非常詭異,不像是嫌惡,不像是憤怒,不像是愧疚,我無法觸及它的真身,卻又感確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也許這只是出於本能的恐懼。我就像是受世界的規矩束縛一樣,就似是它對妄想成為人類的怪物百般阻撓一樣。
我沒有答應他。
當時我十八歲,還記得母親說二十歲就能談戀愛了。之前,我還想著要在二十歲左右找個男友,那我就又能笑話我那畢業時還是單身的姐姐了;然而,我轉眼間就二十歲了。
二十歲是個令人討厭的年紀。
十多歲時,我一直以學業為藉口拒絕裙下之臣對我的好意,更會視早戀的同學為幼稚、不成熟、貪玩。但到了大學,隨著大家認識的人變多,對異性朋友的關係變好,我身邊開始不乏情侶,就連與朋友們的飯聚的話題都圍繞著戀愛,說有人開始戀愛,說自己也想戀愛,說自己找到了對象⋯⋯
有次,我妹一臉驚訝的跟我分享她男友早前就在追求自己,我不以為然,因為這不是甚麼特別的事,而且很容易看出來。我以為我妹早就知道,但她還是表現得很驚訝,嘴裡還重複著「只有我不知道嗎?」
「這是甚麼驚奇的事嗎?」我稍稍提高了音量,諷刺著她。她把下巴收起來,盯著我看,思考了幾秒後,又冷靜地斷言「也是。」「那有沒有甚麼事是會令你驚訝,是你實在沒有想像的?」我又抬起頭,微微仰視著比我高半個頭的妹妹,等待她說出我心中的答案:「你開始談戀愛!」
對他們,屬於那邊的人而言,我談戀愛,就像是天方夜譚,畢竟我也如此認為。
我不會說自己是個遲鈍的人,由於我喜歡觀察和分析別人的言行,我察覺到的事比其他人還要多,只是很多時候會因缺乏經驗而不會輕易下定論而已;但無論是我察覺到的事,還是那些「結論」我都不感興趣。
別人的感情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全都只是一個又一個「事實」,一個又一個由事件的主角自己下結論的事實,與我無關,無法在我心中掀起任何一點漣漪。
我能分析、想像、理解大部分感情,甚至是連環殺人犯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即使別人一輩子都無法接受,一輩子都無法理解,一輩子拒絕與那些野獸共情,我也能解釋他們那滿得溢出來的感情;但唯獨是戀愛,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要作出承諾,為什麼不能作出承諾?為什麼能與人如此親密?為什麼會愛上一個人?為什麼會不再愛一個人?怎樣才算是愛上一個人?這一切對我而言都是如此的不合理,我無法理解,感覺像是一條又一條自相矛盾的公式被隨便堆疊在一起,又無法將乾淨整齊地分類和排列,令我起雞皮疙瘩,甚至有噁心反胃的感覺。我努力解開一條一條的方程式,一個又一個的難題,但「愛情」這道爛題卻又如被放進褲袋的有線耳機,解來解去只令它越纏越緊。我最終放棄了思考。
「愛」就像是小說中,由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字組成的一段段劇情,這一切可能只是機遇巧合,只是為了劇情張力和作者的喜好而出現的劇情,這一切都是作者說的算。現實如戲,愛情都是作者說的算,背後甚至可能沒有任何邏輯可言。
背後有「作者」撐腰的虛構作品:電影、小說、漫畫、動畫、歌舞劇⋯⋯才算有幾分真實和邏輯,而現實的親密關係、情侶、愛昧關係、愛情,更荒謬不合理,虛幻不真實卻又真實存在。
正因如此,我才會討厭這個年紀,這種對我而言不真實的東西在這個時候佔據了我視野的每一個角落,無時無刻都傳到我耳中,更不斷在我腦海中浮浮沉沉。
明明感情一事與我的距離如此近,就像是能在我耳邊輕聲細語的距離,但在我看來,它就是在鐵籠的另一邊。那如冬日早晨時的太陽般溫暖的手只要穿過鐵籠之間的空隙,便能觸碰到我,但我們仍處於兩個不同的世界。
自升上大學,大家自然就會說起談戀愛,說是大學必做的五件事之一,同學們的話題也圍繞著戀愛,甚至有位中學同學擔心我交不交得到男友,只懂讀書的我實在不懂。
即使離開了校園,回到家中我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家妹早就到了談戀愛的年紀,她沒有上大學,總是在家中無所事事,只懂大聲喊著自己想談戀愛甚麼的;最近她終於如願以償,且她男友又常常到訪我們家,又與家妹表現得特別恩愛,令我想見不到他也難,令我不想起「戀愛」也難。
母親第一次見到家妹的男友後,她問我甚麼時候也交個男友。看得出母親並非出於想抱孫的心情問我,她有四個女兒,我姐姐的女兒都已經三歲了,我母親根本不會缺孫子,她只是好奇我會不會也帶男友回家而已。那時我想都沒想,斬釘截鐵的說:「不會,我不會交男友。」
「那算吧,不交就不交。」她如此回應我。
原本我與母親獨處時,我便自然地撒起嬌來,甚麼事都求助於母親,表現得像一個孩子而非一個已經二十歲的大學生。但就在最近,母親問我戀愛的事時,圍繞著我的一切彷彿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我已經到了談戀愛的年紀,已經到了該有另一半的年紀,已經到了不該獨自一人的年紀。
但有些事,並非人人都懂,我不懂。無論妹妹解釋多少關於男友的煩惱,我都不懂,所以即使是特別理性的我,聽著家妹的煩惱,也只會越來越煩躁。
那種感覺就像是大部分學生面對試卷上一條比一條更難的數學問題時,因無從下手而生的煩躁和無助感,又如一個沉重的鉛球,把我獨自留在了「放棄」的深潭之中。
而我又照本能似的躲在其中。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閱讀—我的旅遊小伙伴」為主題,舉辦2025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我們期望藉着這項結合閱讀與創作的比賽,鼓勵兒童及青少年擴闊閱讀領域,深化閱讀層次,讓閱讀開啟知識大門,拓展視野,豐富人生。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閱讀—我的旅遊小伙伴」為主題,舉辦2025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我們期望藉着這項結合閱讀與創作的比賽,鼓勵兒童及青少年擴闊閱讀領域,深化閱讀層次,讓閱讀開啟知識大門,拓展視野,豐富人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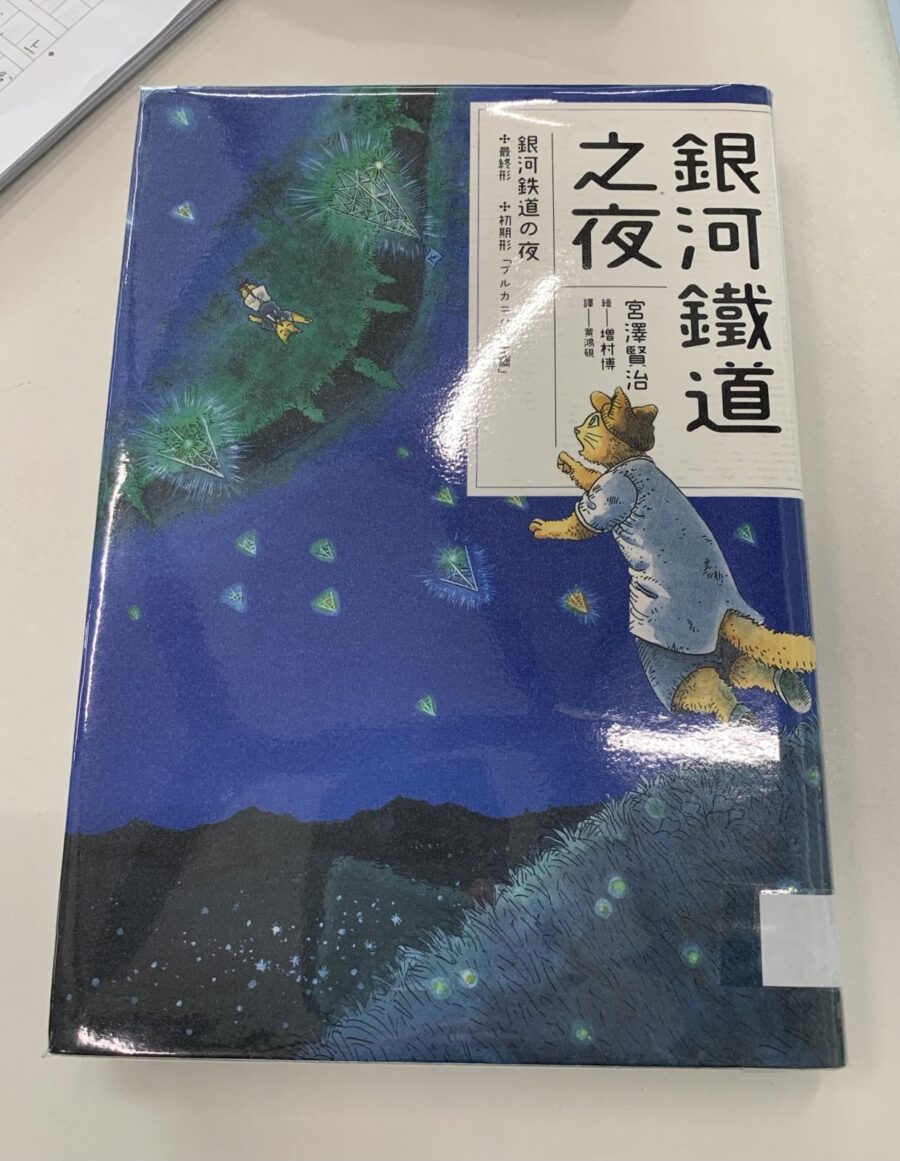 當列車駕離月台差不多半小時後,比葉嘉才發現梓乙一直坐立不安。她意識到有事情發生,徐徐回頭,才發現非亞並不在座位上。他留了下來。梓乙說出了這個守住了半小時的「秘密」。比葉嘉沒有怪責梓乙沉默不語,更沒有怪責非亞不辭而別。他們早有預感,當列車愈來愈接近終點,陸陸續續會有乘客下車,各自尋找他們歸宿而去。最先應該是明月松,然後到阿孟兒、將雲⋯⋯不,最先是小珊妮,一個比葉嘉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
當列車駕離月台差不多半小時後,比葉嘉才發現梓乙一直坐立不安。她意識到有事情發生,徐徐回頭,才發現非亞並不在座位上。他留了下來。梓乙說出了這個守住了半小時的「秘密」。比葉嘉沒有怪責梓乙沉默不語,更沒有怪責非亞不辭而別。他們早有預感,當列車愈來愈接近終點,陸陸續續會有乘客下車,各自尋找他們歸宿而去。最先應該是明月松,然後到阿孟兒、將雲⋯⋯不,最先是小珊妮,一個比葉嘉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